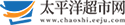蔡磊| 张定宇医生对我说:“这事我一定支持!”
蔡磊著,《相信》,中信出版社2023年4月
把自己捐出去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2021年秋天,陈功教授的Neu Excell Therapeutics公司完成了上千万美元的Pre-A轮融资,原位神经再生技术治疗渐冻症的动物实验终于可以着手启动了。
我的融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但200多场路演失败和无数次与投资人沟通无果,让我开始重新思考这条路的可行性。起初我的想法是自己做一只风险投资基金,筹集资金后,我作为资金管理人,把钱投到相应的药物研发项目上。但如前所说,我的病情发展无法准确预期导致投资基金的高度不确定,以及渐冻症药物研发自身的高风险性,都指向一点:这个思路跑不通。
我开始考虑换一种方式,即不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资金募集,而是以自己的专业性、影响力和资源,为诸多愿意参与这一方向研究的科研团队和机构提供支持、合作、赞助与协调,为他们找钱。也就是说,我的角色从项目发起人变成资源协调人。
比如2021年,高瓴资本、高山资本等大型投资机构都比较关注iPSC(诱导多能干细胞),有意投资该方向,我跟他们数次沟通,其中霍德生物等iPSC公司的科研实力和实战能力都很强,我多次向投资者推荐。2021年年底,霍德生物完成B轮融资数亿元,由高瓴创投领投,礼来亚洲基金及老股东元生创投跟投。
霍德生物CEO范靖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理学学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神经学博士,后来又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细胞工程所道森(Dawson)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脑卒中的机制及靶点10余年。2017年,她回国创立了霍德生物,致力于开发iPS细胞,旨在用健康的功能细胞移植替代神经损伤和退行性疾病中死掉的神经细胞。这也是目前国内外热门的研发方向。
2021年年初我们结识时,她主要研究将iPS细胞疗法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和脑卒中,并且成果显著,相关药物已经在着手进行中美新药临床研究申报(IND),即将进入临床试验。了解我的情况之后,范靖博士一直非常上心,积极帮渐冻症患者制定了iPS细胞疗法的治疗方案,并且把霍德生物渐冻症药物的管线提前。在病理、药理的基础研究,药物研发的路径和治疗方案,以及推动临床前试验等方面,我和团队也尽力为其提供了有价值的专业支持。
希望越来越大。但不可否认,两年多来,病情的持续恶化让我即将丧失工作能力,资金也在持续消耗。
在生病之前,钱之于我只是一个数字,起码保证生活衣食无忧没有问题。但现在,钱却成了摆在我面前的头号难题。面对药物研发领域,自己实在是太穷了。从2020年开始投入上千万元的资金到数据平台、运营管理、基础科研、动物实验、药物研发、投资基金和慈善基金等,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一分钱的收入。目前支持业务的团队成员已经多达几十人,每年投入巨大。
公司账上的资金也就还能支撑我们几个月。
子弹快打光了。
我在想,我还能做点什么?
随着这两年和科学家的不断交流,我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虽然患者大数据平台对于药物研发非常有用,但要想推进基础研究,光有大数据模型是不够的,还需要真人的病理样本。到目前为止,关于渐冻症的重大发现几乎都是在渐冻症患者遗体的标本上发现和验证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患者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的科研样本。有一个院士科学家团队,正渴望研究这些渐冻症样本。他们甚至说,只要给100例渐冻症样本,他们就可能在病理和病因方面有重大发现。
所以,我还有最后一颗“子弹”,就是自己的身体。
其实遗体捐献这个想法我从生病之初就有。早在2020年,有一位病友大姐就和我说:“蔡总,你能不能联系北医三院,拿我的身体去解剖,去研究这个病?”起初我以为她是开玩笑,并没有当真,然而她隔三岔五地就会问我,于是我们深聊了一次。我问:“你为什么想要捐出身体?”
大姐说:“我快70岁了。我有幸福的家庭,有孝顺的子女,还有可爱的孙子,此生没有什么遗憾了。看到你们才40来岁得这个病,我觉得上天对你们不公平,所以我想能不能把我的身体捐给医学家,让他们解剖我,找到病因,就能把大家更快救活了。”
我深受震动。作为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渐冻症所需的研究样本是人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这是无法在患者生前或在活体上进行研究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患者捐献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作为科研样本来进行研究。然而在这方面,中国仍未起步,此前国内还没有一例渐冻症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的样本。
我知道大姐不是开玩笑,犹豫再三后,我把她的意愿转达给了樊东升医生。樊医生也非常感动。渐冻症至今病因不明,而病理研究对促进医学界对这个病的了解和攻克至关重要。
然而,后来才知道捐献的流程很难打通。神经科医生在渐冻症方面是专家,但取脑组织和脊髓组织则需要病理学家来操作,整件事少不了多方的协调和配合。不过,即便知道困难重重,这两年多来随着我对这个病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捐献身体的想法也越来越清晰。没有样本就没法研究,既然之前没有人推动这件事,那么现在我来推动。
2022年年初,我找到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赵洪涛理事长,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说:“我的身体一直在往下滑,所以想跟你商量,如果我去世了,我想把自己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捐献出来,推进渐冻症患者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捐献工作。我知道中国这方面的案例非常少,所以我就想着我来牵头做这个事……但一个人捐对病理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我希望号召更多的渐冻症患者共同捐献,最后努力给医学发展解密渐冻症带来一些帮助。”
医学科研需要的是大数据,只有一两个样本远远不够。所以光我一个人捐还不行,我必须发动足够多的病友在去世后捐献出自己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形成足够大的样本量,才有可能给整个渐冻症领域的研究带来质的变化。
听我说完,赵理事长非常感动。他说:“我做这个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感谢你和其他渐冻症患者的大爱之举,我们当然全力支持!”
我接着说:“这个事情的法律、法规、流程我完全不了解,涉及哪些相关部门,我也不知道,所以也恳请您给予指导。”
随着社会文明伦理的提升,捐献遗体、器官的新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的话题,但渐冻症患者的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标本的提取却是一件极为特殊且困难的事情,对于提取标本的时间、完整性和技术都有极高的要求。由于脑的特殊性,最好在捐献者去世后6小时内、最长不超过24小时拿到大脑标本,才能确保脑组织得到高质量的保存效果,从而达到研究的需求。这不是一般医院可以做的,据说国内顶尖医院也只有病理科的个别大夫能熟练完成这种提取操作。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器官捐献的工作,推动了整个体系在中国的建设,但脑组织和脊髓组织的捐献,之前他们也没有涉足过。但赵理事长很坚定地表示:“蔡磊,你这个事情本身就很伟大,也是我们一直在倡导推动的,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赵理事长迅速联系了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简称“脑库”)发起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
段树民院士是我国脑科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2012年他牵头建立了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此前,因为国内没有一个规范化运行的人脑组织库,中国科学家要研究完整的人脑组织,往往需要向国外的脑库申请,而跨国运送生物样本的法规限制、高昂的费用和复杂的运输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各种脑疾病的发病机制而言,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大脑组织是否一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未解之谜。
那时候在段院士等专家的支持和带领下,中国人脑库一步步发展,于2019年入选科技部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并被命名为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这是中国第一所标准化收集、储存各种神经、精神疾病患者和正常人所捐献的死亡后的大脑,以及他们的病史资料(匿名)的机构,可为全国的神经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人脑组织样本。
“脑库”经过10年左右的建设,成立了中国人脑组织库协作联盟,目前已经有19个规范化建设的人脑组织库,共收集了400多例样本,主要涵盖常见神经、精神疾病以及无脑部疾病的对照全脑样本,而罕见病的标本却一例都没有。
听了我的汇报,段院士说:“蔡磊,你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你可能会改写中国脑库的发展历史。”
他第一时间牵头拉了一个大微信群,群里包括现有19个“脑库”的负责人、几十家医院和科研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十几位神经内科专家。从那时起,我们这个群里定期开会讨论渐冻症患者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捐献的事。
要做成这件事,首先要有一定数量的渐冻症患者愿意做出捐献。其实从2022年年初确定了要做这件事时,我就开始和病友聊。先是一对一地单独沟通,尤其是和每一位病友见面的时候,我都会直接问:“如果那一天到了,你愿不愿意捐献出自己的身体?”
这个问题对患者及其家属来说是无情的,甚至可以说有违人道。没有人想面对死亡,不但患者自身很难接受死亡这件事,患者家属更难以接受。去世后遗体还需要被解剖、被提取或者是作为样本被参观,很多人心理上很难过这一关。别说捐献身体了,我记得小时候还见过因为不让土葬而引发的冲突事件,传统观念让我们对身体的完整性看得非常重要。其实这件事我也考虑了很久,但目前研究样本在中国几乎没有,总需要有人迈出第一步。
因为平时有了信任基础,很多病友都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并表示积极支持。有位北京的病友当即表示:“蔡总,不光我自己捐,我让全家人都捐!”这让我特别感动。也有些人表示要再考虑一下。这种犹豫,有时候是因为暂时不想面对。一位患者的丈夫说:“我想让妻子保持好心情,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件事。”我对他说:“同意捐献并不会导致我们死亡,而是会增加我们生的希望。”
单独沟通了几周之后,我在覆盖上万名的病友群里正式发布了这条倡议,呼吁大家捐出自己的身体,为渐冻症的攻克做最后的贡献。我发起了捐献意向接龙,蔡磊第一个,马上有病友接龙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个月大家报名很积极,很快积累了四五百人,之后报名速度逐渐放缓,到5月份的时候,数字停在了700上下,很多天没有再增加。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停止挨个去跟病友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也在直播里不停地宣讲捐献的意义。虽然直言死亡非常痛苦,但再痛苦也要跟大家说。快200年了,渐冻症的病因、病理都还没弄清楚,我们怎么办?唯有自救。只有通过建立一定数量的渐冻症患者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样本库,才有可能找到破解渐冻症的方法。
“如果在10年前、20年前,就有大量患者做遗体以及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捐献的事情,可能我们今天就不会死掉。同样,尽管我们现在很绝望,但可以通过这个举动给下一代病人带来希望,这个世界才能越来越好。”
当然,也有人强烈质疑我的动机,在病友群里指名大骂:“蔡磊就是为了诈骗病友的遗体!”
我又气又想笑。这个“诈骗”的成本有点高,因为在操作过程中我们才知道,脑组织和脊髓组织捐献这件事推进起来到底有多难。